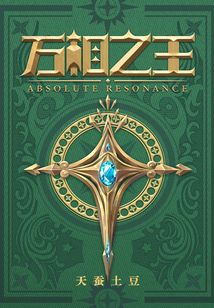她知道自己是突兀了。平日裡從來都未曾關心過的人,這個時候,這般殷勤,也難過別人不生出不該有的心思來。
「張家嫂子,我家裡還有事,我就先走了!」梁姚氏再也站不下去了,在張嬸的眼光之下,梁姚氏覺得自己內心那一些小九九都無處遁形,嚇的她落荒而逃。
梁姚氏失魂落魄地往家裡走。心情很是不好,想到剛才在顧家發生的事情,心裡就如打翻了調料罐子,酸甜苦辣啥都有。
「回來了?」梁木匠正在院子裡做一張桌子,見梁姚氏無精打採的回來,關切地問道:「還是沒見著?」
「沒有!」梁姚氏有些無奈,憂鬱地說道。
「下次就別去了,去了也看不著,你心裡也難受。還不如不去!」梁木匠並沒有停下手裡的活,勸道。
「哎,我這心裡,愧疚啊!」梁姚氏說著說著,眼淚就止不住地流了下來。
梁木匠見自己老婆這個樣子,連忙緊張的朝周圍看了看,慌忙說道:「小點聲,小心別讓人聽見!」
「聽見又怎麼了!」梁姚氏賭氣地說道,還特意沖著顧家老宅大聲地說道:「現在是什麼世道,這人善被人欺,馬善被人騎,這做了錯事咋還能這麼囂張跋扈!」
「好了,好了,你小點聲!」梁木匠連忙上前捂住了梁姚氏的嘴,急迫地勸到:「我的好祖宗,咱不在外面說這話,咱回屋裡說去吧!」
「當家的,我心裡難受啊!」梁姚氏眼淚水止不住地流,無奈地說道:「我膽子小,不敢說。可是你看這幾個孩子,被欺負成啥樣了。我於心不忍啊!」
「於心不忍又能怎樣?咱們無憑無據地。」
「當家的,我跟你說,那天曹氏去婉丫頭家裡鬧事,我後來不是也在場嗎?當時場面很混亂,我跟曹氏也打了起來,後來我就問了一句曹氏,我問曹氏,你這樣對婉丫頭,你對得起顧老二夫婦嗎?」梁姚氏低聲說道:「你猜後來怎麼著?」
「怎麼著?」梁木匠一聽,也問道。
「那曹氏跟見了鬼一樣,心虛地爬起來就跑了!」梁姚氏說道:「這曹氏心裡對這事可是清楚的很。」
「哎,她清楚,咱們也知道。隻是,咱們沒有證據,單憑咱們兩張嘴說說,誰相信呢?輕點地,說不定還把咱們趕出村子裡,這要是重一點,說不定那曹氏心一狠,也把咱們給幹了!」梁木匠一說起曹氏這個女人,心就發麻。這女人,看著柔柔弱弱,萬種風情的,怎麼發起狠來,那麼地心狠手辣。
「……」梁姚氏一聽,低下頭來不說話了。
「我也奉勸你一句,咱們離這人遠一點……」梁木匠意味深長地指了指顧家的老宅,繼續說道:「想要離這家人遠一點,那一家人也要離遠一點!」
「可是……」梁姚氏還想要反駁,梁木匠直接打斷了她的話:「別可是了,在這吳溪村裡面,就咱們兩個人相依為命,我們能不去招惹別人,就別去招惹!免得惹禍上身,到時候,怎麼死的,會不會有人替咱們收屍咱都不知道!」
想了想,梁木匠更是哀嘆:「這顧家二房死的時候,還有四個子女披麻戴孝、哭墳燒香,可是咱們要是死了呢?」
「當家的,我……」梁姚氏聽出了梁木匠心裡的惆悵,心裡很是內疚。
「別說了,我不怪你!我啥都不求,我隻要你好好的,陪在我身邊,我就知足了!」梁木匠安慰地拍了拍梁姚氏的肩,溫柔地勸道。
「當家的!」梁姚氏見梁木匠這般樣子,心裡更是難受。成親這麼多年,什麼方法都試過了,就是懷不上。
梁姚氏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自己做錯了事,這是老天在懲罰自己,日子一天天流逝,這心裡從剛開始的急迫,到後來的失望,再到現在的絕望,這不爭氣的肚子怎麼就是沒有一點動靜。
對於孩子的事情,梁姚氏已經不做任何的指望和期待了。但是對於梁木匠,梁姚氏心中有愧!
她生不出孩子,可是梁木匠對她卻是不離不棄,這麼多年來,陪著她一起折騰,雖然沒有結果,梁木匠也放棄了,但是,對於梁姚氏,梁木匠剛成親的時候怎麼對待她,這麼多年過去了,在沒有生下一兒半女的情況下,還是怎麼樣的對待她!
梁姚氏心中充滿了感激。
聽見自己當家的這麼說,梁姚氏心中就算對顧筱婉一家再愧疚,也不能為了這個事情,毀了自己個的家。
說到底,人心都是自私的!
從去玉書學院上課的第一日起,顧寧安就認真的對待老師上的每一堂課。
因著他們是剛剛入門的學生,就像師娘所說,他們的啟蒙學習,由徐承澤教授。
徐承澤別看年紀輕輕,卻沉穩冷靜。而且,知書達理,愛書如命。
顧寧安從小勝子那裡得知,徐承澤十來歲就考中了秀才,是整個劉家鎮年紀最小的秀才。心裡對這位小先生是充滿了尊敬與崇拜。發誓要跟著這位先生好好學習,這樣才能對得起為自己操持的姐姐。
而徐承澤對這位雙生子的學生,心裡也是喜愛的很。別看是從農村裡面出來的,但是教養、舉止、禮儀樣樣都不比旁的鎮子上的學生差。
這顧寧安更是有讀書的天賦,字寫的端莊大方,一教就會,難得的是個省心的學生。顧寧安好學,這徐承澤又愛才,自然而然的,有時候就會多教一點知識。這一來二往的,徐承澤倒有些把顧寧安當弟弟看待了。
而顧寧平則不一樣,他來學院裡面學校,有一點不習慣。整日裡學習讀書、習字背課,對顧寧平那自由的性子來說,不可謂不是一種折磨。